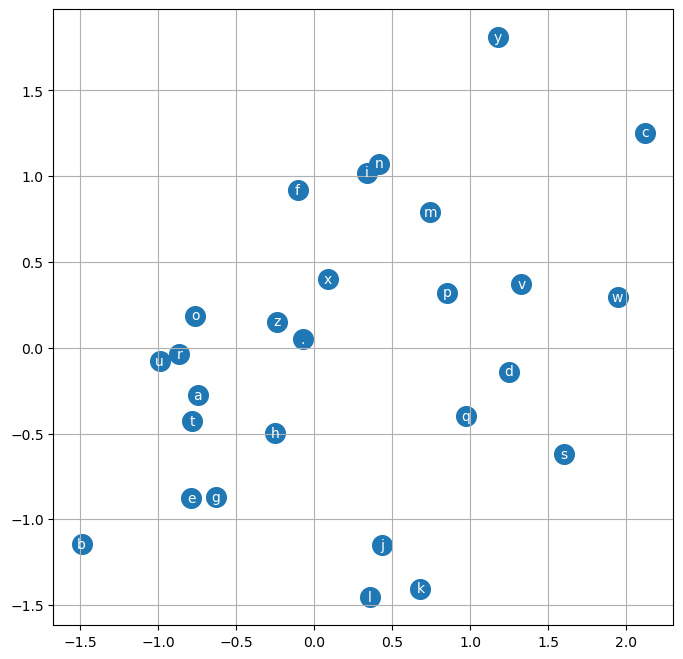
空无所空
Insights Chinese 《悉达多》读后感
在一个忙碌又空闲的星期四下午,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读完了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。想到上一次这样畅快而迫不及待得读完一本书还是在高中。真是一场有趣的旅程,从婆罗门到沙门,遇见乔达摩而后坠入尘世,最后在河流边明白“自我”。最后这一幕颇有鲁智深在六和寺圆寂时“钱塘江上潮信来,今日方知我是我”之感。
在一个忙碌又空闲的星期四下午,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读完了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。想到上一次这样畅快而迫不及待得读完一本书还是在高中。真是一场有趣的旅程,从婆罗门到沙门,遇见乔达摩而后坠入尘世,最后在河流边明白“自我”。最后这一幕颇有鲁智深在六和寺圆寂时“钱塘江上潮信来,今日方知我是我”之感。
一开始,出身优渥的悉达多因为灵魂的悸动不安,为了追求“永恒的平静和幸福”而离开家人朋友,跟随沙门踏上征途。高三那年春天,因为疫情的影响不必上学,我经常在周末沿着西湖周围长跑十几公里。那时我最喜欢的一条路线就是从植物园开始,沿着灵隐路一直跑到上天竺。长跑的中后期,身体肌肉的酸痛,呼吸的急促令我的精神格外放松,什么都不需要思考,只需要向前迈步。长跑时的精神状态与苦修的沙门近似,通过肉体的疲惫换取精神的休憩,只是沙门要求更高。
然而,这并不是悉达多想追求的,他认为尽管可以通过苦修和冥想,达到“无我”的境界,但是回归却不可避免。同样的“逃避”也可以通过饮酒等方式达成。他后来在林中与佛陀辩论,明白了佛陀的法义并非是最宝贵的东西,真正的价值在于彻悟过程中的过程和体悟,而这又是难以言说的。正所谓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”。要么以一种非常规的话语(海德格尔的being)表达出来,要么以一种异常普适而庸俗的言语,《易》有云:“庸言之信,庸行之谨。”可以侧面的证实。对于文字语言工具的批判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做过了,“哲学是语言的暴政”。然而悉达多并非一无所获,当他遇见伽摩罗—-那个教会他爱的人时,身无长物,衣衫褴褛的男人这样说,“我会思想,我会等待,我会斋戒”。于是,凭借这些,他便得到了尘世中,几乎一切他想要的东西。
当时我想长跑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忙碌的学业。后来,高考结束后,因为离开了所在的地方,逐渐减少了跑步的次数和距离。然而这一段经历却留下了些许雪泥鸿爪,每当上无聊的课时走神,我便回想起那个初春,从眼前飞过的景色,从喧嚣的大路到宁静的寺庙,从老人到小孩。我相信,这段经历构建了类似“庇护所”的记忆,它还会继续影响着我,在将来的某一天促使着我转变。
我想起高中的一位厉害的同学在自我总结中引用的一句话,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,仍旧只是一粒麦子;若是落在地里死了,就会结出许多粒麦子来”。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;于天上看见深渊。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;于无所希望中得救”。年老的悉达多面对河水,自惭形秽而想要自觉与此时,他受“唵”的指引,重新复生。他向船夫学习,习得了河水的教诲:
“世界自身则遍于我之内外,从不片面。从未有一人或一事纯属轮回或者纯属涅粲,从未有一人完全是圣贤或是罪人。世界之所以表面如此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幻觉,即认为时间是某种真实之物。时间并无实体,侨文达,我曾反复悟到这一点。而如果时间并非真实,那么仿佛存在于现世与永恒,痛苦与极乐,善与恶之间的分界线也只是一种幻象。”
《清静经》云:“观空亦空,空无所空。”悉达多从俗世的梦幻空寂中醒来,像圣人一样步入林中,步入“万物的圆润统一”。亦也像海德格尔在《田间路》中写的:
“一切都朝向同一者说着弃绝。弃绝不拿。弃绝给。它给出单纯之无尽力量。这一消息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在家里,在一古老的本源中。”